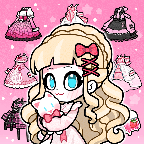| 廣西新聞網 > 首頁欄目 > 首頁要聞 > 正文 |
二合一平板电脑排名 |
2025-10-04 16:57 來源:廣西云-廣西日報 記者 羅莎 楊思悅 通訊員 劉鵬飛 編輯:馮芯然 |
|
大學宿舍的封城是個狂熱的游戲迷,對星際的著迷程度超過我們任何一個人,他是山西人,瘦瘦小小,戴個眼鏡,說話口音挺重,但脾氣挺招人喜歡
大學宿舍的封城是個狂熱的游戲迷,對星際的著迷程度超過我們任何一個人,他是山西人,瘦瘦小小,戴個眼鏡,說話口音挺重,但脾氣挺招人喜歡。 大二下半學期宿舍樓拉上了網線,我們以學習計算機的名義陸續買了電腦,封城從中關村扛回一臺簇新錚亮的組裝機,以 TNT2 Pro 顯卡為首的一水主流配置,花了八千多塊,還不包括一臺大功率的 UPS 電源。 我們都對色彩明艷的 19 寸特麗瓏顯示器垂涎欲滴,封城卻做了個驚人的決定,他買張小桌子,把電腦擱在他靠門上鋪的床上,設了 BIOS 密碼,拉個小簾子,宣布從此電腦不再公用。布簾后面是他的隱私空間,要聯網打 Hunters 地圖喊一聲就成,但想借他的電腦看片玩游戲,對不起,欠奉。 我們一開始很不理解,喝酒時候灌了封城幾回,得知他買電腦的八千塊是挪用本學期學費加上三個月的生活費才湊夠的,輔導員和學校財務每天找他要錢,他每天拖延,已經被學院約談好幾次了。 王強當時氣得一板凳砸了半箱燕京啤酒,說:「封城你現在去中關村給我把電腦退了,我們雖然是沒把大學當回事兒的瞎胡上,可說到底還不是為了混張畢業證,你看老六上大一的時候掛了那么多課,上學期一口氣重修補考了七門,小抄做得好都過了,你看看你到現在還有六個掛科沒有重修,倒連學費都欠著不給,的不想畢業了嗎你?」 封城紅著臉打著嗝,說:「大學算個屁,畢業證算個屁,老子將來要當職業星際選手,等老子練熟了克隆技術和三線APM,速出隱刀一砍一個準,閃電矩陣指哪打哪,到時 Grrr、Yellow 和 Boxer 在老子面前算個鳥蛋,WCG 分分鐘奪冠,暴雪的名人堂里必定有老子一號!從現在開始誰也別勸我上課,老子這一輩子的追求就是星際了,不服,單挑,贏了我再廢話!」 王強捋起袖子準備揍他,我們在旁邊使勁摁住,他氣喘吁吁說:「封城你有種,咱們現在就回宿舍去連星際,我贏了,你明天早上就到村里去退電腦,你贏了,我從此再也不說一句廢話,你愛干嘛干嘛,死在簾子后頭我他媽都不多看一眼。」 王強放開鼠標,失神地瞧著失去連接的星際畫面,老四掀起上鋪的簾子看看,發現勝利者已經趴在鍵盤上睡著了,兩腿之間不知何時吐了一大灘,戰況激烈,沒人發現。 那個暑假,封城跟學校說回家干農活,打電話給父母說在學校工作,在校門口溜達一圈回了寢室,就再也沒出宿舍門。 老二在動物園批發市場打工賣酸辣粉,每天晚上回寢室給封城帶一份酸辣粉加肉夾饃,要不是有他,封城沒準會餓死在床上。 據老二描述說他根本沒看見過封城下床,小便拿個大可樂瓶尿進去,床尾堆了一排裝滿的瓶子,大便不知怎么解決;也沒看見過封城吃東西,給他吃就吃,給他喝就喝,不給就不吃不喝,時時刻刻盯著屏幕,嘴里念念叨叨。 老二說早晨一睜眼就看到封城在玩游戲,晚上下班回來看連姿勢都沒變,有時候半夜被尿憋醒,仍能看見封城的簾子后面透著紅黃藍綠的光。 我們宿舍沒有誰愛干凈,每個學期床單枕套也總要換兩次的,封城則不同,他整整一年沒有換洗過床單被套,藍色棉布變成某種怪異的灰綠色,身旁墻壁油膩膩的,頭發一縷一縷黏在頭皮上二合一平板電腦排名。 封城將吃剩的酸辣粉和肉夾饃塞進塑料袋丟在床上,北京的夏天悶熱,剩菜隔天就酸臭撲鼻蒼蠅亂飛,可封城本人渾然不覺,仿若屏幕之外的世界對他來說不過鏡花水月,真實的宇宙和生命意義只存在于游戲之中。 有一天老二實在忍無可忍,爬到床上把封城的尿瓶和垃圾一股腦清理干凈,指著他的鼻尖說這樣下去不行,立馬下床洗澡換衣服曬床單。 封城的眼神魔怔地盯著老二的臉,似乎能透過他的皮膚看到后面的索尼特麗瓏屏幕,雙手噼里啪啦在鍵盤和鼠標上飛舞。 老二僵硬地扭回頭看,發現封城剛完成了一個漂亮的克隆操作,三艘海盜船釋放的網完美封鎖了四輛坦克和兩個地堡的火力,神族部隊一擁而上沖破防線,對手立刻打出了「gg」。 老二打了個寒顫,慢慢爬下床,把簾子拉好。用他的話說,封城已經瘋了,以前認識的那個封城不在了,現在坐在床上的是個怪物二合一平板電腦排名。 那會兒剛工作沒幾年,工資勉強夠租房子坐公交買泡面,鼓足勇氣才敢吃個米飯炒菜,攢倆月錢去洗一回腳,交個女朋友都沒錢給人家買禮物,整天拉著手在公園里閑逛等天黑,一邊提防戴紅箍的老頭老太太一邊親嘴兒,有時候回家一看,滿的包。 大學同學結婚時候一般不好意思打電話,畢業幾年不聯系,怎好意思開口就要份子錢,學理工科的情商再低也沒這么厚臉皮。他們會發個分成幾截的長短信,說一通久不聯系十分想念的廢話,追憶過去,展望未來,分析國際局勢,討論職業前景,胡扯大幾百字,然后在短信末尾仿若不經意地說:「哦對了哥們,我下周六上午十一點在西外大街郭林飯店辦婚禮,有空的話一定來啊,給你留倆座位,離舞臺最近的。回見!」 收到這種短信的時候,我會特別淡定地回到出租房,把地板仔細拖干凈,鋪上報紙,將枕頭被子堆在報紙上,自個兒爬上書桌,大吼一聲,把手機狠狠地往地上一扔。砸完了,撿起手機回條:「恭喜哥們兒我一定帶著伴兒參加」;再給女朋友發個:「明天不去開房了啊有點事兒」,然后躺在地上邊哭邊數錢。 窮日子過了幾年,同學陸續都結婚了,我倒成了單身,因為有回大冬天夜里裹著羽絨服在玉淵潭公園湖邊樹林里親熱被紅箍老太太的手電筒框住了,女朋友藏在衣服里不敢露頭。 老太太說:「別以為我沒看見,你這下邊兒可是四條腿兒啊。建文明城市,這地兒可不讓瞎搞,交罰款吧。」 我把掛在樹上的褲子兜翻遍了才找出四十五塊錢,老太太非要一百,討價還價半天,最后從羽絨服側兜里找出五個鋼镚兒湊了五十,不給開票。老太太走了,我回頭一看,女朋友嘴唇都凍青了。 她給我一個大嘴巴子,說:「要不是我體格好早他媽湊合不下去了,今兒就今兒,掰了!」然后抓起衣服裹上羽絨服就走,害我穿著個毛線衣在零下十二度的北京城足足走了四個小時才回到出租房。 一回去我就蹲客廳哭了,一方面心疼,一方面腳疼,合租的哥們兒說:「你丫傻了吧,打個車回來我給你掏錢不得了。」 份子錢給得差不多了,工資也見漲,原以為窮日子算是過到頭了,誰知兜里還是沒錢,照樣上班下班混吃等死,買地攤貨租房坐公交煮泡面,最大的娛樂就是跟合租哥們喝酒扯淡,偶爾去個洗頭房洗滌身心,當然限于收入,不能常去。大學同系得越來越少,大家結婚之后都關起門過小日子去了,沒有婚禮,就沒了聚會的機會,感情這玩意兒肯定是越遠越淡。 這天是周末,我正在屋里玩游戲,短信鈴聲響了。現在已經過了怕看短信的年紀,以為是 10086 發來的信息,就沒看。打完一局抓起手機一瞧,我愣了,煙頭掉在大腿上把大褲衩燙了個洞。 王強先發了個意義不明的文字表情,然后說:「今年七月份是畢業十周年紀念,本班自從畢業后就沒搞過同學會,這次無論如何也要聚一下,不許出差,禁止請假,七月一日中午十二點在學校南門大鴨梨烤鴨店見面,家屬就別帶了,有車也甭開,肝不好的提前喝藥,喝醉是必然的。不見不散。」 我根本沒覺得畢業有這么久了。我把手機放下,推開窗看了一眼,城市邊緣的居民樓密密匝匝,街邊停滿黑色和白色的汽車,手機店放著流行歌曲,煎餅攤圍滿了人,杭州小籠包門口蒸籠摞得老高,自行車歪歪扭扭從歪脖子樹旁繞過,一切跟十年前沒有分別。 有時候覺得窗子被時間凍結了二合一平板電腦排名,大學時從宿舍樓窗戶向學校圍墻外望,看到的也是如此密集的樓、擁擠的車子,蒸籠雪白的蒸汽,窗間過馬,俯仰之間就老了十年。 王強是同學里最早結婚的一個,那會兒我還領實習工資,沒錢上禮,包了張白條寫著「新婚志喜隨禮伍佰元沒錢暫欠有錢時兌現」,王強當時沒說啥,到現在也沒找我要錢。我總覺得對不起他。 第二天早晨一睜眼,手機上有條王強發來的短信,還是說:「畢業十周年聚會所有人必須參加不得請假,七月一日中午大鴨梨不見不散。」 我猜他是收到太多短信看不過來,干脆群發統一回復了。王強從上學時候就這樣,做事兒咋咋呼呼,脾氣大,容易發火兒,但為人仗義,是個正格兒的山東漢子。 看看日歷,離七月一日還有兩周半,我回頭瞧瞧亂七八糟的出租屋,覺得這他媽都是什么事兒啊。同學會從來就是件扯淡的事情,我參加過一次高中同學會,基調就是有錢人勾搭女同學,窮鬼蹲一邊兒喝悶酒,吃完飯出門,該開車的開車,該開房的開房,沒出息的自個兒等公車回家。 沒錯,我就是那個沒出息的窮鬼,窮到漂亮女同學向我傾訴家庭不幸的時候都不敢搭腔。我知道借著點酒勁把肩膀一樓,準能出門小旅館開房直奔主題,但我不敢。 王強復讀了幾年,年紀比我們大一截,身高體胖,一臉胡子茬,分宿舍第一次見的時候我們都管他叫叔叔,宿管阿姨死活不信他是學生,非要輔導員到現場驗明正身。后來大伙陸續報道,王強幫每個人搬東西,辦手續,買暖壺水盆飯盒,拾掇柜子,發床單兒被罩,鞍前馬后跑著,跟家長一模一樣。 213 宿舍一共住了七個人,沒空調沒電視,那年頭的宿舍就這條件。按年紀排輩,王強是老大,免不了帶兄弟們喝個酒吹個牛,說點同年同日死的酸詞兒,網吧刷刷夜,吐過幾回,打個群架,關系就鐵得很了。 剛開學,誰都會裝模作樣學習學習,早晨七點爬起來吃早飯,上課坐前排,老師提問勤舉手,晚上戴耳機去上自習,一邊聽英語錄音帶,一邊做高數題。倆月之后,原形畢露。該談戀愛的談戀愛了,該睡懶覺的不起床了,三食堂旁邊的租書店火了起來,每次輔導員查寢宿舍樓里都哀嚎一片。 小樹林里躲躲閃閃凈是情侶,一到晚上,湖邊坐滿雙頭四臂的詭異人影,仿若一眾魑魅魍魎在涮火鍋。人人都參加社團,動機沒有一個純粹的,圖書館的破 586 電腦得排隊用,一個人掃雷,十個人圍觀,連操場都成了熱門場所,人們有時候實在沒地兒去,翹課打籃球直到天黑。 那時候誰都沒電腦,想玩游戲得去校外小網吧,十塊錢。可那會兒一個月生活費才五百,前半個月夜夜笙歌,后半個月饑寒交迫,饅頭蘸辣椒醬吃多了會變得眼睛發綠,火燙。后來學校機房對外開放了,非計算機系的學生也能花錢上機,只有局域網,五毛錢一小時,213 宿舍集體早起去計科樓門口排隊,去晚了就沒好機子了,機房最老的那批電腦,除了軟驅就沒有一個部件好用的。 那時候星際爭霸剛出來沒多久,在大學里一下子火了。我們整天窩在機房用 UDP 連星際,選個富礦圖,七個人打一個電腦,戰況緊張激烈,有時候還會打輸。會輸不是因為技術差,是因為機房鼠標用得年頭太久,滾輪磨成了橢球形,動作再溫柔指針也會無規則漂移,要想準確操作部隊,一方面依靠邏輯思維能力,另一方面,純靠人品。 世界上就是有這么一種人,長得比一般人好看點兒,腦子比一般人聰明點兒,家里比一般人家有錢點兒,跟大伙一樣吃食堂、看武俠、翹課打游戲,走在人群里不顯眼,也不愛出風頭。可一群人在校園里遛彎碰見漂亮姑娘問路,姑娘不找別人,準問他;期末考試大伙紛紛掛科,他門門都在及格線上面;每個月底我們饅頭抹辣椒醬,他能從馬哲課本里翻出張十元鈔票請我們吃二食堂的大肉龍,老五就是這么一個人見人愛的主兒。 那天晚上我們集體翹了選修課在寢室玩大老二賭毛票兒,王強從樓下小賣鋪拎了一件啤酒,我們一邊抽著兩塊錢一包的都寶香煙,一邊就著水煮花生喝燕京啤酒。有人推開門的時候,酒喝了半箱,桌上堆滿零錢,滾滾濃煙中一群紅臉漢子呆呆坐在賭桌前,老六弱弱地叫了聲老師。 從那天晚上起我們再也不用去計科樓機房排隊。學校西門外開了一家叫藍宇的黑網吧,網吧藏在曲里拐彎的小巷子里,當然沒有招牌,老板打通六層樓房頂樓的三間民宅,塞了五十臺電腦進去,每小時一塊五,通宵八塊,沖卡還能打八折。 學校附近早有一間正規網吧,窗明幾凈,一水兒的聯想電腦,屋里香噴噴的,收銀臺代賣咖啡,憑我們五百塊一個月的生活費,進去通幾個宵就得破產。黑網吧則是老板自己從中關村拉來的兼容機,15 寸雜牌純平顯示器,風扇噪音大得像飛機起飛;房間里永遠充滿煙味、康師傅紅燒牛肉面味和臭腳丫子味,椅子依地形放得犬牙交錯,伸懶腰動作大點能打著后排人的后腦勺,拖鞋一離腳立刻被踢到電腦桌深處,買瓶水要是不蓋蓋兒,一會兒就漂滿死蒼蠅和煙灰。 我們記不清在藍宇網吧打過多少次通宵,吃過多少紅燒牛肉面加榨菜火腿腸,抽過多少兩塊錢一包的都寶香煙,多少次在局域網開黑 4V4,多少次天光剛剛放亮時候搖搖晃晃離開網吧,走到巷子口的早點攤兒上吃油條喝一大碗熱乎乎的豆腐腦,聞著城市剛剛蘇醒的看早起的上班族蹬著自行車從各條胡同里鉆出來,匯入越來越熱鬧的大街。 通宵完了回宿舍補覺,自然就翹了課。我們會派一個代表去上必修課,倘若老師點名,偷偷溜出教室打電話回來通報。那時候還沒手機,整層樓只有一臺 IC 卡電話,電話一響,靜悄悄的樓道立刻炸窩,所有人跳出被窩踩著拖鞋抓著上衣沖出宿舍,奔跑在北京晴朗的秋日里面。 老三說:「臥槽昨天打 Lost Temple 2V2 太投入一晚上沒變姿勢到現在腿還麻著呢。」 遺憾的是,就算一路狂奔,也經常被記缺勤。那學期期末的時候我們幾乎人人都掛了科,只有老五所有課程門門及格,馬哲還拿了個漂亮的 98 分。 我自恃雙眼視力 1.5,排在學號前一位后一位的又是每天自習到深夜的好學生,考前突擊翻了兩遍書,自覺只要好學生的胳膊肘不礙事,考試準能答個 80 分以上。倒霉的是考模擬電路時老師打亂學號排列,本宿舍的一群學渣坐成梅花樁陣勢,我被圍在正中間,無論往哪個方向瞟,都是一張雪白干凈的試卷,加一張滿是油汗無助的臉。縱使老五從教室角落隔空拋來小紙條,也沒法救眾哥們兒于水火之中了。 寒假是場災難,通知單寄到家后遭到男女混合雙打,本以為高中畢業就不挨揍了,誰知還是被抽得哭爹叫娘。好不容易開學回來,還得從生活費里擠出重修費,一個學分兩百塊,交錢那天大伙都咬牙切齒對天發誓說再也不去網吧刷夜了,誰去誰是狗。 在自習室裝模作樣坐了一下午,王強偷偷摸摸地遁走,我跟在后面,回頭一看,全宿舍都跑了出來,汪汪汪叫著奔向藍宇網吧。 人這玩意兒,說變就變。姑娘的心思你捉摸不了,男人其實也一個尿性,印象中是那時喝酒打架連星際的兄弟,一見面變成了滿嘴心靈雞湯的保險銷售員,你跟他聊過去,他跟你聊理財,你想知道他現在過得好不好,他只關心你的職位和年薪,這種心空空蕩蕩無處懸掛的難受,只有住過集體宿舍的人才曉得。 坐在窗口瞧著外面,北京郊區的巷子在熱風中悶著,騎自行車的大爺摔倒在馬路牙子,塑料袋里的雞蛋碎了一地。大爺躺在那兒叫喚,有個小伙子走過來瞧瞧,轉身進了路邊的網吧,網吧窗戶上貼著大字:兩元一小時十元會員卡充一百送一百買泡面送火腿腸。 我想了想,跟我上大學時候的物價似乎沒什么變化,盯著網吧瞧了一會兒,越來越覺得熟悉,從網吧二層防盜網圍著的窗戶望進去,那泛黃的純平顯示器、日光燈管旁邊飛舞的蛾子、吧臺柜子上層落滿灰塵的幾瓶洋酒、墻上神族狂熱者的海報,一切跟當年的藍宇網吧幾乎一模一樣。恍惚之間,那些發光的屏幕前坐著年輕時候的我們,那舉著泡面叉子指點別人分兵操作的,不正是剛剛長出胡子的我嗎。 我打了個激靈,仔細一看,一切都變了,網吧是嶄新的,里面坐的失敗者也是嶄新的。大爺推著自行車一瘸一拐走了,塑料袋滴滴答答流著黃湯,柏油路上的雞蛋眼瞅著就快熟了。 這時候手機滴答一響,又有短信進來,王強說:「對了有空去看看那誰吧,好長時間沒去了,總躲著也不是個事兒,得了見面再說吧,別遲到,遲到罰酒,喝死了算。」 這個詞扎得我胃里一疼,像喝了杯冰冷的二鍋頭,里面還泡著根凍得梆硬的魚刺兒。平常上班下班吃飯玩游戲睡覺,日子過得平靜而沒啥指望,回憶之類的東西都在后腦勺的淤泥里面沉著,黏黏糊糊,不把頭殼敲爛,根本挖不出來。 我去冰箱里拿瓶燕京啤酒,拿牙咬開瓶蓋,坐進客廳沙發,仰脖灌了半瓶。室友從屋里歪脖看我,說:「你丫大白天喝什么酒啊是又跟姑娘掰了?來打把 2V2 把我的戰績刷成超炫酷的 200 勝 50 負,請你出去吃羊肉串嗑毛豆喝不摻水的扎啤,不過結賬還是 AA 啊。」 我的酒量也就一瓶燕京,半瓶下肚覺得暈暈乎乎,打開電視,上面在播西游記。我開始想王強說的那個人。從腦子的淤泥里一挖,腐爛發臭的東西一咕嘟浮了出來,剛提起開頭,就揪出一串,想撇開已經黏了一手,甩不掉,撕不斷。 我們宿舍的封城是個狂熱的游戲迷,對星際的著迷程度超過我們任何一個人,他是山西人,瘦瘦小小,戴個眼鏡,說話口音挺重,但脾氣挺招人喜歡。最早搬進宿舍的電腦就是封城讓家里寄來的舊聯想,奔騰 233 的 CPU,128 兆內存,3.2G 硬盤,15 寸純平顯示器,開機進 windows 得六分鐘時間,從點擊 Star Craft 圖標到開始游戲,足足要等十分鐘。 但我們把電腦像寶貝一樣擺在桌子正中間,早晨六點半來電,準有人跳下床打開電源,嘴里叼著牙刷,搶著玩第一把;晚上十一點停電之前,屏幕前必定擠滿了腦袋,不是看日本,就是為了 Grrrr 和 Slayer boxer 的比賽吵翻天。那年暑假有幾個人沒回家,宿舍不斷電,老電腦日夜開著,兩個月之內從來沒人碰過關機鍵,除非它因為系統崩潰和過熱而藍屏重啟。 大二下半學期宿舍樓拉上了網線,我們以學習計算機的名義陸續買了電腦,封城的舊聯想功成身退,被收破爛的用五十塊錢收走搬上三輪車。老電腦退休的第二天,他從中關村扛回一臺簇新錚亮的組裝機,以 TNT2 Pro 顯卡為首的一水主流配置,花了八千多塊,還不包括一臺大功率的 UPS 電源。 我們都對色彩明艷的 19 寸特麗瓏顯示器垂涎欲滴,封城卻做了個驚人的決定,他買張小桌子,把電腦擱在他靠門上鋪的床上,設了 BIOS 密碼,拉個小簾子,宣布從此電腦不再公用,布簾后面是他的隱私空間,要聯網打 Hunters 地圖喊一聲就成,但想借他的電腦看片玩游戲,對不起,欠奉。 我們一開始很不理解,喝酒時候灌了封城幾回,得知他買電腦的八千塊是挪用本學期學費加上三個月的生活費才湊夠的,輔導員和學校財務每天找他要錢,他每天拖延,已經被學院約談好幾次了。 王強當時氣得一板凳砸了半箱燕京啤酒,說:「封城你現在去中關村給我把電腦退了,我們雖然是沒把大學當回事兒的瞎胡上,可說到底還不是為了混張畢業證,你看老六上大一的時候掛了那么多課,上學期一口氣重修補考了七門,小抄做得好都過了,你看看你到現在還有六個掛科沒有重修,倒連學費都欠著不給,的不想畢業了嗎你?」 封城紅著臉打著嗝,說:「大學算個屁,畢業證算個屁,老子將來要當職業星際選手,等老子練熟了克隆技術和三線APM,速出隱刀一砍一個準,閃電矩陣指哪打哪,到時 Grrr、Yellow 和 Boxer 在老子面前算個鳥蛋,WCG 分分鐘奪冠,暴雪的名人堂里必定有老子一號!從現在開始誰也別勸我上課,老子這一輩子的追求就是星際了,不服,單挑,贏了我再廢話!」 王強捋起袖子準備揍他,我們在旁邊使勁摁住,他氣喘吁吁說:「封城你有種,咱們現在就回宿舍去連星際,我贏了,你明天早上就到村里去退電腦,你贏了,我從此再也不說一句廢話,你愛干嘛干嘛,死在簾子后頭我他媽都不多看一眼。」 倆人把桌子一掀走出飯店,我們忙不迭在旁邊護著,老五在后面把賬結了追出來,那會兒是晚上八點多,校園里到處都是人,王強和封城在路上咋咋呼呼叫喚,要單挑的消息就一下子傳開了。當時教育網的速度很慢,我們在局域網架了一個名叫 BlueFan 的星際服務器,封城在 BlueFan 的記錄是 255 勝 127 敗,排名前十,但戰績不算突出。 王強雖然長得五大三粗,手速是我們之中最快的,靠著 6D 速狗和刺蛇海戰術獨霸一方,戰績是驚人的 144 勝 29 敗,雄踞排行榜亞軍。這倆人要打賭單挑,驚動了整個服務器的玩家,BlueFan 的管理員親自建立 Lost Temple 地圖選擇旁觀模式等待兩人加入,在那個時刻全服只有這么一個主機存在,所有人都停止戰斗準備觀戰。 我們宿舍擠進了三十多個人,連陽臺都占滿了。王強紅著臉坐在桌前,一邊等自己電腦開機一邊摳出鼠標滾輪擦拭,封城鉆進上鋪的簾子后面,羅技超級旋貂 MX300 的紅光一閃即逝。 人群之中露出老四細長的脖子,他偷偷觀察簾子里的情況,說封城的酒勁上來連眼睛都睜不開了,這時候單挑必輸無疑。 王強放開鼠標,失神地瞧著失去連接的星際畫面,老四掀起上鋪的簾子看看,發現勝利者已經趴在鍵盤上睡著了,兩腿之間不知何時吐了一大灘,戰況激烈,沒人發現。 暑假歸來,老六因為上學期掛科較多被請家長,他爸爸在學院辦公室外當場脫下老六的褲子打,打得噼啪作響,全學院的女生都看見了,這出苦肉計換得老六勉強升上大三,而我們這種每回掛一兩科的廢物學生并不在老師的視線范圍內,也順利變成大三學長,可以在社團勾搭大一學妹了。 封城留級了。他期末考試八門課掛了七門,包括但凡出勤就能通過的體育課,唯一在及格線以上的是選修課《青春期性保健》,他令人驚訝地拿了個高分。 輔導員坐火車趕到封城五百公里之外的老家,把成績單往他父母的院門口一貼,轉身就走。封城的父母扔下鋤頭在后面追,拉著老師的手痛哭流涕。 輔導員說:「這孩子腦子是很聰明的就是轉不過彎來,玩游戲能當飯吃嗎,大學生每天不學習窩在宿舍玩游戲期末考試考得一塌糊涂,這樣的學生留著是禍害,要處分,要開除。」封城父母懇請老師給個機會,一定好好教訓孩子。 原來封城跟學校說回家干農活,打電話給父母說在學校工作,在校門口溜達一圈回了寢室,就再也沒出宿舍門。那個暑假老二在動物園批發市場打工賣酸辣粉,每天晚上回寢室給封城帶一份酸辣粉加肉夾饃,要不是有他,封城沒準會餓死在床上。 據老二描述說他根本沒看見過封城下床,小便拿個大可樂瓶尿進去,床尾堆了一排裝滿的瓶子,大便不知怎么解決;也沒看見過封城吃東西,給他吃就吃,給他喝就喝,不給就不吃不喝,時時刻刻盯著屏幕,嘴里念念叨叨。 老二說早晨一睜眼就看到封城在玩游戲,晚上下班回來看連姿勢都沒變,有時候半夜被尿憋醒,仍能看見封城的簾子后面透著紅黃藍綠的光。 我們宿舍沒有誰愛干凈,每個學期床單枕套也總要換兩次的,封城則不同,他整整一年沒有換洗過床單被套,藍色棉布變成某種怪異的灰綠色,身旁墻壁油膩膩的,頭發一縷一縷黏在頭皮上,奇怪的是靠近他鋪位卻不覺得惡臭,只有種淡淡的酸味,可能臟得太厲害了,反而達成了人與污物的和諧共生。 不過那個暑假老二常被臭味困擾,因為封城將吃剩的酸辣粉和肉夾饃塞進塑料袋丟在床上,北京的夏天悶熱,剩菜隔天就酸臭撲鼻蒼蠅亂飛,可封城本人渾然不覺,仿若屏幕之外的世界對他來說不過鏡花水月,真實的宇宙和生命意義只存在于游戲之中。 有一天老二實在忍無可忍,爬到床上把封城的尿瓶和垃圾一股腦清理干凈,指著他的鼻尖說這樣下去不行,立馬下床洗澡換衣服曬床單,封城的眼神魔怔地盯著老二的臉,似乎能透過他的皮膚看到后面的索尼特麗瓏屏幕,雙手噼里啪啦在鍵盤和鼠標上飛舞。老二僵硬地扭回頭看,發現封城剛完成了一個漂亮的克隆操作,三艘海盜船釋放的網完美封鎖了四輛坦克和兩個地堡的火力,神族部隊一擁而上沖破防線,對手立刻打出了「gg」。 老二打了個寒顫,慢慢爬下床,把簾子拉好。用他的話說,封城已經瘋了,以前認識的那個封城不在了,現在坐在床上的是個怪物。 我沒能喝完一整瓶燕京,酒還剩個底兒,我歪在沙發上睡了。睡得并不安穩,亂七八糟做夢,一會兒夢到王強,一會兒夢到老二,上學時候我跟這兩個人關系最好,雖然號稱七兄弟,也有親疏遠近。 像老三老六就走得近,倆人剛開始一點兒都不和睦,同時追機電二班的一個女生,為這事兒沒少打架,后來那女生跟民族大學的一個帶刀漢子搞在一起,倆人覺得同病相憐,喝酒吐著吐著就成了鐵哥們。 老六重修課考試有一半是老三替考的,因為老三作弊的技術最好,把課程重點敲進電腦,用宋體四號字、行間距 0 磅、4 分欄打印成密密麻麻的蠅頭小字,裁成小紙條一圈一圈纏在鋼筆的墨水管上,擰上筆帽,神仙也看不出來,遇到危急時刻把筆管一撅,墨水溢出來浸濕紙條,能做到死無對證。靠這招老六幫自己和別人度過了不少難關。 畢業以后老四成了美容會所的職業減肥師,每天的工作是往闊太太們身上一圈一圈纏保鮮膜,我覺得這大概是因果循環。 我醒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了,室友還在那兒玩星際,看我一眼,說:「你丫倒是心寬坐那兒就睡著了,剛才房東敲門收房租我假裝不在家沒敢開門,可你丫睡就睡吧還打鼾,鼾聲跟火車拉笛似的隔著兩層樓都能聽見,實在沒轍開門把房租交了,這下飯錢都沒了吃什么串,喝西北風去吧。」 我回到屋里,坐在窗邊點了根煙,抽兩口掐了。我這個人就是這樣,抽煙喝酒玩游戲打牌泡妞,可煙抽不多,酒量不大,打牌沒癮,泡妞沒錢,游戲玩多了頭暈惡心,就打星際這個癖好十年如一日地堅持了下來。 上浩方打了兩局 Luna 地圖單挑,都輸了,我總覺得我挺厲害,照照鏡子,還是個,跟當年沒什么兩樣。 記得大學時候有次喝酒,王強說:「以后咱們這群人里面最有出息的指定是老五,老五一定能成個大人物,我們其他人都是」。 我當時不服氣,站起來說:「王強你丫別跟這兒損人,今天把話給你撂這兒,我他媽的以后混出個模樣讓你們看看我究竟是還是!」 十年以后,老五成了企業高管,我是一個租住在城中村的碼農,每次有人想組織大學同學會我都拒絕參加,因為沒臉見他們。這次王強組織十周年聚會,我內心是抗拒的,但他提到了「那個人」。 大三開學,封城留級了,本來學院給出開除學籍的處分,他爸媽坐長途汽車來到大學,拿土雞蛋和甲魚堵住了的嘴。雖然是農民,承包了果園和魚塘的老兩口并不算窮,當下交齊封城欠的學費,請、、輔導員和幾位老師在高粱橋無名居吃了頓奢侈的淮揚菜,開除學籍改成了留級查看,大三開學,封城變成了大二學生。 他爹媽走的時候給我們宿舍搬了箱自家種的蘋果,懇請我們幫忙照看獨生子,封城卻坐在簾子后面玩游戲連聲招呼都不打,氣得王強坐在那兒呼哧呼哧喘氣。老五解釋說封城得抓緊學習把拉下的課補上,在電腦上學習圖形軟件沒空分心,請老兩口諒解,兩位老人欣慰地連連點頭,掀開簾子看了兒子五分鐘,轉身背著彩條布包走了。 老五坐過來跟我商量,說:「封城現在這副模樣不是個辦法,長此以往人就廢了,得想轍把他從床上揪下來。」 當天晚上我和老五沒有去網吧刷夜,一邊聽收音機里的前列腺保健節目,一邊在陽臺抽煙聊天。十一點零五分,宿舍熄燈了,樓道里響起一片哀嚎,封城的簾子后面還幽幽亮著光,他的 UPS 電源能讓電腦多工作十五分鐘,十五分鐘可以多打一把 1V1,這就是封城的執著。 老五說:「生氣也是好事兒,你看封城一頭埋在星際里面,七情六欲都沒有了,生氣起碼還是正常人的反應,要不生氣那問題才叫嚴重了。」 老五說:「電源線不值錢二十塊錢買一大把,我準備把他的機箱電源搞壞,到中關村換個電源一來一回一天時間,好歹讓封城出趟宿舍樓。」 老五說:「封城模擬電路從來都沒及格過,他看不出來,再說發現了就賠他唄,大不了把我電腦的電源換給他。」 終于簾子后的光消失了。我們望著靠門的上鋪,借外面街燈的亮光隱約看到封城的輪廓,他在屏幕前呆呆地坐了十分鐘,仿佛在腦海中打完剛才的一局游戲,然后直挺挺地栽倒在床上,后腦勺接觸枕頭發出沉悶的撞擊聲,嚇了我們一跳。
報紙版面截圖。 |
|
掃一掃在手機打開當前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