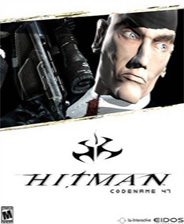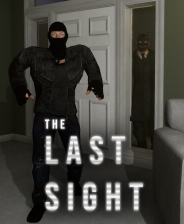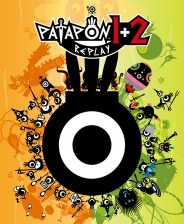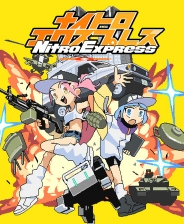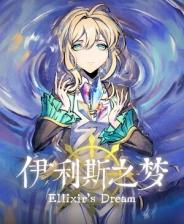| 廣西新聞網 > 首頁欄目 > 首頁要聞 > 正文 |
电脑怎么直接重装系统桌面壁纸高清全屏电脑 |
2025-10-04 16:57 來源:廣西云-廣西日報 記者 羅莎 楊思悅 通訊員 劉鵬飛 編輯:馮芯然 |
|
去年10月,我偶然得知《智族GQ》的合作攝影師張博然通過給父母上網課的方式,重新梳理家庭關系,并堅持了半年多時間
去年10月,我偶然得知《智族GQ》的合作攝影師張博然通過給父母上網課的方式,重新梳理家庭關系,并堅持了半年多時間。我對這件事最早始于“沒有人會這么做”的新奇,成年之后,子女與父母的關系能夠“相安無事”,已是幸事,為何還要花精力去重新教育?然而,接下來三四個月里發生的事情,像一塊吸鐵石把我拽回了家。 在這個過程里,我一邊焦慮無措,一邊又像大力水手吃了菠菜一樣,莫名其妙地變得成熟堅強。我和張博然的交流也擁有了非常實際的動力。我看完了他幾乎所有的網課視頻,有我能做到的,有我做不到的,也有我不會選擇做的。我想他的這場家庭教育實驗不一定適合每個人實踐,但或許能提供一種面對家庭的思路。 張博然是1990年生人,成長于四線城市河北承德的一個小康家庭,父母在當地機關單位工作,臨近退休。作為獨生子,他18歲去北京上大學,畢業后留京工作,去年又搬到上海。在去年春天幾個月里,他工作減少,思考變多。在一些契機下,他決定給父母上網課。 從情感交流方式上,這是一個很典型的中國家庭。父親強勢,大男子主義,在孩子幼時忙于工作,常年疏于家庭照顧,對妻子缺乏理解與體貼,并且不覺得這有什么錯處;母親被動,視家庭和兒子為生命的全部核心,在長期打壓下步步隱忍退讓,委屈卻不敢言,內心有改變生活的微弱火苗但缺乏出走的勇氣。 面對家庭,張博然有復雜的情感。小時候他同情母親,抵觸父親,極力避免成為他,但當自己進入親密關系時,又處處發現父親的影子。經過疫情三年,他關于“什么是最重要的”的想法發生了變化,他不想把父母甩在身后,不想將來面對父母就是在病床前照護的那一刻。 上野千鶴子的書提到,30代(30~39歲)是過渡期世代,是新舊交替的一代。他們不得不處理新思想和舊傳統的矛盾。這種掙扎體現在婚育、事業選擇,也體現在與父母、家庭的代際割裂。 以18歲進入大學為起點的20代(20~29歲),是逃離原生家庭的過程。我們感知到“家”會傷人,在想怎么離開家,怎么擺脫父母超強的控制欲。在離開家的10年時間里,我們獲得了一些自由,自我逐漸長成,對原生家庭在自己身上留下的心理和行為模式越發清晰。簡單說,我們在厘清和處理“生長痛”。 而當進入30代,父母開始轉向老齡、需看護的狀態。衰老使得他們被迅速變化的時代甩在身后,也進一步削弱了他們在家庭中的控制力。對很多90后而言,這是一個主動或被動地回歸原生家庭的過程。 我們一起算過一筆賬,兒女30歲左右,父母大多在55到60歲。這個階段,他們先后退休,生活一下變得空蕩(因此迫切希望兒女結婚生育),但他們身體尚可,仍有行動的自由,仍有體驗生活的愿望。張博然希望他們借助觀念的變化換一種活法兒,重新擁有幸福的能力。這樣等到身體機能進一步衰退的70歲,他們會少很多遺憾。 他對父母的“家庭教育”從一些奇怪但必要的原點開始,比如教會父親第一次對母親說出“對不起”,他驚訝地發現父親年近60歲,竟然沒有道歉的經驗;他鼓勵母親學會開車,這是通往新生活的信心;他還引導父親送花、寫賀卡,訂浪漫餐廳(這一點失敗了),第一次笨拙地表達了“愛”。 更多的課是關于家庭決策。“如何處理房產”“要不要買掃地機器人”“催表妹生孩子有什么不對”,這些在張博然的家庭課堂上是一樣重要的,都要畫思維導圖來分析,拆解出邏輯漏洞。 在父母面前,建立起“當老師”的權威是困難的,因為這需要調轉過往的權力關系。我想張博然的家庭教育實驗能夠推進,基于他一直經濟獨立,也基于這是一個有諸多問題但相對平等、仍有對話可能性的家庭。更直接的原因可能是,他幫助父母處理了一處有成為爛尾樓風險的房產,直接挽回了近百萬的損失。這讓他在家庭中擁有了更高的話語權。生活很瑣碎,也很實際。 這也并非一場完美的教育。不管在課堂上還是在日常生活里,他們常常爆發沖突,那種“父親的影子”會重新籠罩張博然,在一些時刻,他仿佛成為了當年的父親,他會發脾氣,失去耐心,感到挫敗,并釋放出壓迫感。在他的課堂筆記和我們的交流中,他逐漸對此覺察,也意識到自己其實也在“被教育”。在構建更理想的家庭關系之前,這是不完美但必要的探索。 第一次跟父母溝通上課的想法是去年5月7號,我提了兩點,一是我覺得大家活了一輩子也可能不知道怎么活,我們現在能不能重新學習,換一種活法兒?二是我們三個人能不能一起做一件事,就是共讀一本書。我很動容,說得都是肺腑之言,他們能感受到我和平常不一樣。 三天后,計劃啟動。當天的課堂記錄我寫道,第一次給父母上課,兩個半小時,他們接受度還可以,但能明顯感覺不適應,有排斥感,下次縮短時間試試,多增加他們發言和討論的過程。 每年暑假我都會去山村給孩子們上攝影課,積累了些教育經驗。我發現我父母恰好是兩類最典型的學生:我爸是那種刺頭,愛接話茬兒,喜歡表現但又不求甚解;我媽是那張非常被動的學生,不善于發言,有點膽怯,因為長期被丈夫打壓而不敢表達自己。 我用《把時間當做朋友》做教材,這本書通俗易懂,但對他們還是門檻過高。一開始我發現他們連基礎的閱讀理解能力都沒有,課本讀得磕磕絆絆,斷句總是錯誤,鬧了不少笑話。一切都只能從頭教起。我對教材進行了大量改編,因為書里提到的例子都是哥白尼馬基雅維利,距離他們生活太遠了,我就拿我們仨生活里遇到的問題來舉例,從爛尾樓怎么處理到要不要買掃地機器人。這一下就拉近了他們和知識的關系,他們能馬上意識到,學這個對自己有用。 在父母面前,建立起“當老師”的權威是很困難的。我想的辦法是,首先我要讓他們獲得實際的好處,比如我處理好了“爛尾樓事件”,我做的家庭投資決策被證明是正確的;其次,“利用”他們的需求。我媽的需求是,她很想我,需要我的陪伴,希望從兒子這里獲得理解和關注。只要跟她打打電話,她就很開心,那上網課完全能滿足這一層次的需求。對我爸而言,單位的晉升與復雜的人際,讓他黔驢技窮,他有急需解決問題的需求。 就這樣,以每周一到兩次的頻率,我給父母磕磕絆絆上了三個月網課。八月,我從上海回承德,我期待親眼見證他們的改變,但沒想到線下第一課是竟是給父親上的道歉課。 一天晚上,我處理完工作,發現我媽眼圈紅紅的,快哭了或者剛哭過。我先問了一圈,弄明白事情大概是這樣的:我爸在那兒弄手機,我媽一會兒問他要不要吃這個,一會兒問他要不要喝那個,其實是關心他,但我爸很不耐煩,他平時罵罵咧咧慣了,就脾氣暴躁地挑我媽毛病、罵人。 我架起手機(以留作課堂記錄),讓他倆坐在沙發上互相溝通。我爸一開始理直氣壯,說里面有誤會,我媽忘記告訴他什么事了,他很煩躁。我說,無論什么都不能構成你罵人的理由。她遺漏了某些信息,你可以詢問,你可以解釋,但不能罵人。我要求我爸向我媽道歉。 我爸不情愿,我媽不說話,場面就僵持著。很快,我媽就妥協了,說哎算了吧。她覺得一輩子都這么過來了,我爸啥時候道過歉。但我非常堅持,讓他們把手機放下,不準干別的事。如果不道歉,這個事情就沒完。當時我就在觀察我爸的狀態,你能感覺到這樣的處境是他這輩子都沒有遇到過的,他從來沒有主動向別人道過歉,也從來沒有人教他或者強迫他去道歉。 這反而更誘使我去push他。我想,天哪,我爸50多歲了,竟然從來沒有道歉的經驗。而我媽已經完全習慣了受委屈,不做任何反抗。我今天一定要試試改變這個局面。 經過幾番說服,我爸答應配合。他第一回是這么說的,“行了,剛才我那什么,沒問清,下次注意。”這種語言方式就暴露了他所有的行為模式,一切以自己為中心,絲毫不考慮別人的感受。 我指出,這不叫道歉。道歉非常簡單,三個字就夠。結果我爸的第一反應是,哪三個字?他疑惑的表情絕對不是裝的,他是真的不知道這三個字是什么。這時我媽破涕為笑。我看著他憨厚的樣子,也有點哭笑不得。接著我爸開始找這“三個字”,他又說了一回,“我錯了,行了吧。” 在這一瞬間,我仿佛看到了無數中國的中年男人和妻子相處的縮影。我就在想,為什么家庭和社會沒有教給那一代的男性說“對不起”?以至于這都成為陌生的經驗。 我說,這樣道歉是不對的,如果不會你可以上網查查。我爸聽完還嘚瑟起來了,“這有什么上網查的,不就是‘我錯了’三個字嘛。”這會兒我媽笑得眼淚都噴出來了。 他又試了一回,“我道歉,行了吧。”我說你這兩回說得還行,但為啥一定要加“行了吧”這三個字?這時已經過去將近40分鐘了,他的狀態從一開始的茫然不知所措,到迫不及待地想要從這個處境里逃走,再到敷衍應付,此刻已接近惱羞成怒。 我媽又站出來打圓場,“行了行了,差不多得了”。我意識到她也不想在這個環境里待著,因為結婚30多年了,次次都失望,也不差這一次。她甚至擔心會因此破壞了家庭氛圍,爆發更大的爭吵。但我覺得只有push到我爸的心理極限,才能真正觸及他的問題核心所在。 我讓自己平復下來,向我爸解釋,你仔細想想你剛才的情緒對不對?道歉是讓對方感受到你真誠的歉意,而不是完成道歉行為。我媽看著我爸,像過去每次爭吵中那樣,率先妥協,“就三個字,對不起嘛,你說對不起就行了。”我知道我媽是受害者,但我還是有點不開心。任何一個在家庭關系里囂張跋扈的人背后,一定也有一個時刻突破自己原則的人配合縱容。 后來又磨了一會兒之后,他還是會無意識地話末帶上“行了吧”三個字。你會發現這就是他的口頭禪,反映了他潛意識里的逃避、應付、抗拒。因為他有非常脆弱的自我和自尊,他不能進入到自我否定。這也是我在很多男人身上觀察到的,包括我自己。 最終,我爸對我媽說出了“對不起”三個字桌面壁紙高清全屏電腦。他有沒有真正認識到這三個字的重量,我持懷疑態度。我知道這個過程讓所有人都不舒服,我在逼著大家“渡劫”。但再痛苦也一定要磨出來,磨出來之后我相信是在他們心里種下了種子,他們會開始思考問題出在哪兒。 給父母上課,也是對我心境的一種磨煉。中間有好幾次他們打退堂鼓,累了不想學了。這時你就很挫敗,我的課堂筆記里經常出現類似的話,“今天挺平穩的,但是跟父母還有點急。” 去年,我媽正式退休。她一輩子沒出過遠門,沒坐過飛機。她一直跟我念叨,等退休了就可以開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我能感覺到,當她在婚姻和家庭里感到疲憊,她渴望逃離,渴望有屬于自己的生活。 我們這一代父母“看世界”是通過短視頻。我媽之前跟我說,看別人騎行很羨慕,后來又說想學開車,因為看到了一個中年婦女(蘇敏阿姨)開著房車環游中國。在刷到一個喪夫老人拿著錢去泰國獨居后,她還提出要學英語,買了相關課程。我覺得這是短視頻最大的好處,這些例子給予了中老年婦女很多希望,讓她們看到人生存在另外一種活法兒。 我媽想學車還有一個實際考慮,姥姥家距離承德市區有幾十公里,我媽每次看望姥姥都得依賴我爸開車送她。如果我爸工作忙,或者犯懶不想去,我媽就像少了兩條腿。 在學習“如何溝通”的一堂課上,我提出家里要立一個規矩:不論對家人、朋友還是陌生人,多講贊美、肯定、鼓勵、支持,不要吝嗇;不講挖苦、貶低、嘲諷、調侃。我想落實的第一個實踐,就是全家支持、鼓勵我媽學會開車。我媽作為一個被家庭事務禁足了大半輩子的女人,她想要出去看看,距離出發她只差我爸的一句鼓勵了。 我希望她真正地為自己活一次,多考慮自我的感受,勇敢地踏出這一步,不怕被別人打擊否定。先從小事做起,掌握成功體驗。當打開“為自己做成一件事”的思路后,再去做更多的事。 我在課堂上開啟了討論。我爸覺得這不行那也不行,怕他的車磕碰,又嫌請教練浪費錢,最后說要給我媽買個破二手車開。我當時很生氣,因為這暴露了他根本不會關心人。我說到底是車重要,還是人重要?車是為了保護人的,還是人為了保護車啊?你這是把人當做車的緩沖區了。 我越說越激動。我說為什么在你的價值排序里,任何東西都優先于人?是不是你的思維習慣里就沒有把家人當人,沒有把他們放在第一位?你看家里一旦東西壞了,你首先是埋怨別人。 跟他們溝通是需要話術的。我拿他最在意的、工作上遇到的晉升難題舉例。我說為什么你難以處理好單位的人際關系?首先因為你沒有處理好自己家庭的親密關系。你可能覺得在外面人模狗樣,在家里囂張跋扈,可以切換自如。但人的行為習慣是日常養成的,你總會有意無意暴露自己的“尾巴”。更為關鍵的是,行為習慣會反向引導思維方式,當你不關心家人的真實需求,你怎么可能關注到同事和領導的需求?我說爸,你要想解決工作中的事情,最實際的就是對我媽好點,對我爺爺奶奶好點,對我姑姑(你姐姐)好點,你有沒有仔細想過他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我意識到禁錮我媽的東西,比如男權思想和世俗眼光,同樣也禁錮著我爸。他們做事不從自己的需求出發,而是從別人的評價出發。思想觀念越落后的地方,越容易從別人的眼色里做決策。 上完那堂課,我爸的觀念發生了一些轉變。也同意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我媽報了駕校重新學習。我媽第一次去學車,他因為看到新聞上說有私教品行不端對女學員上下其手,還自己偷偷跟過去看了看。我覺得挺可愛的,說明他在關心人了。 我后來私下跟我爸說,我媽會開車,你是第一受益人。你應酬喝酒了不用找代駕,你懶得開車的時候她可以開,你為什么不讓她學?這同樣是一種話術。對于習慣了自私自利、以自我為中心的人,你必須得把邏輯打通,讓他感覺能得到好處,只有這樣他才能慢慢為別人著想。而且通過這件事,我爸發現,我媽自己能干成一件事,他在一點點地改變刻板印象。 尤為重要和特別提及的是,我媽開得真比我爸好!在我媽獨自開車上路的那天,我收到了她的微信,“到家后特別開心,原來習得一項技能真的可以改變一個人,起碼能愉悅自己。雖說過程有些掙扎但最終堅持下來了,謝謝寶兒給媽媽支持與鼓勵,讓媽媽擁有了不一樣的生活和感受。” 大家經常說,人的性格是無法改變的。我不完全相信這句話。我覺得性格是由無數行為習慣組成的,性格是歸納概括,不是前置定義。但我得承認,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父母五十多年養成的原生家庭的行為習慣,怎么可能通過大半年的網課就改變呢?改變只能耳濡目染,潛移默化。 去年的9月30日,是我媽正式退休的日子,這一天也是她的生日。我們家從沒儀式感,但我發現生活是需要儀式感的,儀式感是情感表達的一個機會。很多人會強調,我們中國人內斂,不說I love you,但內斂有內斂的表達方式,你看《隱入塵煙》里塞一塊窩頭,那不也是表達嗎? 提前兩天我就開始訂花,我知道我爸做不來這些事,我想他能完成這個儀式也可以,但一定得讓他參與進來,比如我們分別給媽媽寫一張卡片。我爸知道這事后,第一反應是,不用買,你媽公司給買歡送花了。我心想,公司送的跟你送的,能一樣嗎?公司的禮敬到,做為丈夫的,更應該給到。這對我媽也更重要。 我爸一輩子沒有浪漫過,這對他實在太陌生了。他后來想了想,對我說,還是兒子想得周到,然后開始憋賀詞。最后他寫道,“祝老婆,雙喜臨門,生日退休同慶快樂!愿今后我們全家所有的美好都如期而至,時光與我們同在,幸福伴我們遠行。”我記憶中,這是他第一次用“老婆”這個詞。 那天早上,我爸給我媽做了一碗長壽面。我媽給我傳來兩張照片,是我爸拍的,我媽抱著花,笑顏如開。我看了真高興。我還向我爸提議,你中午帶我媽去吃一個環境好點、有浪漫氛圍、能安靜說話的餐廳。我爸說,都訂好了,我們中午去吃涮羊肉,你二舅他們也去。當時我就無語了,這和我想象中的浪漫約會完全不沾邊,味兒大,吃相不好看,還一群人。最后我爸還給我拍一視頻,大家一起吃涮羊肉挺開心。我想這或許才是他們的舒適區,那也挺好的。 我有個朋友是一個女性公號的主理人。有次聊起我給父母上課的經歷,她覺得有些不可思議,跟我取經,我讓她先從和自己的農村媽媽建立正常溝通做起。當幫助改變了自己媽媽的處境,你所做的女性內容才能更為服眾。畢竟你現在提供的建議,更多是適用一些家庭條件不錯、有選擇權的城市女性,而更為廣大的婦女群體是在視野之外的。我覺得對大部分年輕人來講,傾聽、關心、愛護自己的媽媽,是支持女性的最小可行性方案。 她經常說,跟媽媽說兩句就沒得聊了。我說那是你提供的細節不夠多,溝通頻次又太低。給父母上了10個月網課,50多次,將近100個小時,我覺得最核心也最樸素的,就是培養起了溝通的習慣和互相理解的氛圍。上課無非是給我們仨要經常一起溝通聊天,找到了一個借口。所謂深度溝通,一定是從溝通頻率和長度上開始的。 我認為教育不是自上而下的,也不是先來后到的。好的教育應該是一個可逆的、互補的過程,這也是教育收益最大化的方式。 我也在想,我做家庭教育最隱秘的內心需求是什么?和前女友在一起時,她總覺得我說話兇,分手前還送了我兩本書《親密關系》和《非暴力溝通》。我逐漸發現我的某些行為習慣和我爸如出一轍,但是我小時候明明那么討厭這些部分,極力避免成為他,為什么最后偏偏像他?我很費解。我還跟我爸說過,他聽完很憤怒,也很委屈,“你怎么不學我好的地方?”我后來想明白了,孩子根本沒有能力去辨別,從小就習得了這一切。 所以我想這一切的根源是因為我有一個“討厭的三角”,我討厭我爸對我媽的壓迫、不理解和不體貼;我也討厭我媽的逃避、不反抗和不溝通。我同樣討厭自己對家庭不管不顧,脾氣暴躁。這是一個相互作用、穩定的“三角”結構,厘清他們的問題就是厘清我的問題。 去年年底想明白這一點后,我想把家庭的研究范圍擴大,因為我知道我爸的性格養成與我爺爺奶奶是直接關系的。比如,我爸作為傳統重男輕女家族里的小兒子,養尊處優,從來是家庭的中心,從沒遭遇過挫折。我想往上探究,把爺爺奶奶也納入家庭教育的范疇里。 去年11月,我為一本雜志拍攝《秋園》的作者楊本芬。我和楊奶奶朝夕相處了兩天電腦怎么直接重裝系統。兩天不長,但閱讀了楊奶奶的一生,也因此與她結下忘年交。能在給父母上課的這一年認識她,讓我相信可以稱之為緣分的奇妙連接。通過她,我收獲了很多提點。回程路上我做了一個決定,這次過年我要辦一場家庭讀書會,讀《秋園》,讓家里的女人讀到理解,讓家里的男人讀到自省。 年底感染高峰期,我先中招,想起楊奶奶,發去問候,他們一家也沒能幸免。今年1月,再通信時,驚聞章爺爺去世了。楊奶奶說她很痛苦,我一時不知道如何安慰。“之驊”現在體會的是“秋園”曾經體會過的喪夫之痛。臨近過年,我從書店里帶回《秋園》《我本芬芳》給家人,發了張照片給楊奶奶,希望她能心情好一些。 家庭讀書會的第一場安排在除夕年夜飯后。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姑姑姑父,我和妹妹,我們一家8口圍在一起,我和妹妹輪流朗讀,每個小章節后,我再帶領大家討論。為什么選擇這本書?因為它直接和家庭相關,寫的又是祖輩和父輩熟悉的歷史和生活,他們有無盡的共鳴。我想通過這根引線去了解他們的過去。 爺爺有些精神,聽力不佳,但他上過學,邏輯清晰,對歷史背景如數家珍,發言贏得了大家喝彩;奶奶只上到初中,但她和楊奶奶一樣,是上世紀生活的親歷者,有很多女性才有的生命經驗。我給了奶奶很多發言的機會,并呼吁全家拍手鼓勵。 新年鐘聲響起,我給爺爺奶奶拜年。爺爺說,又一年,又長一歲。奶奶說,這是一樣的公平,不論誰都長了一歲,不論貧富。我常常想,每一位80多歲的家庭婦女,都能講出一部《秋園》,都有機會成為楊本芬。 看著爺爺奶奶,我能感受到一種生活實苦。因為爺爺飽受精神創傷的折磨,多年來他一直懷疑奶奶串通外人來家里偷東西,經常做出一些換鎖、失控罵人的舉動。這兩年我給他家里裝了攝像頭,拿手機監控給他看,我說我24小時幫你看著家,你放心。 2018年的時候,有一次我翻老相冊,看到一張五個人的全家福,多了一個不認識的小男孩。我問姑姑這是誰,才知道我爸原來還有個弟弟,七八歲時去湖里游泳淹死了。爺爺受了很大刺激,這是他精神的來源電腦怎么直接重裝系統。后來誰都不敢提這件事。我才知道這個家庭抹不掉的傷疤在這里。 我猜想這也影響了他對我爸的家庭教育,爺爺更拿他當寶貝了。我最近想寫我自己的家庭志,采訪爺爺奶奶,讓他們多跟我說說話。多年來我也經常給他們拍照桌面壁紙高清全屏電腦,準備出版一本家庭相冊。 今年過年的時候,大家說起這半年的變化,都說看到了我爸的進步。我家三代人里,除了奶奶,只有姑姑還不會開車,我也順勢鼓勵她去學開車。姑姑表示一直想學,看到我媽學成,她也有了動力。我們家的女人現在都開始做自己以前沒想過,或者不敢做的事情了。 許多人都渴望自己能走出原生家庭,我則希望有機會帶著家人一起“走出去”,逃離迂腐傳統的束縛,去找尋各自作為獨立個體的意義和追求;同時,再結伴“走回來”,互相認同,互相擔待,作為家庭整體緊密,抗壓,這能大幅降低不安全感,增加切實的幸福感。 經過這大半年的課程,我爸媽對我的生活也多了很多尊重,催婚催育的頻次降低了。因為他們看到了一種單調重復的人生模板——稀里糊涂地結婚,稀里糊涂地生孩子,然后交給父母帶,給孩子報班,雞娃,競爭,焦慮......他們意識到這不是我,也不是他們想要的生活。 雖然常常重蹈覆轍,但我能看到他們的細微變化。前幾天我和爸媽視頻,發現我媽在姥姥家,她自己開車回去的。新手司機上路開高速,我爸不放心還跟著她。我對我爸有很大改觀。 我的行為開始傳遞了。爸媽也開始往上處理自己的家庭關系,不論是決策能力,還是承擔家庭事務的能力,都有了更多的能量。我爸對爺爺多了耐心,我媽在娘家多了擔當。現在家里遇到什么事情,爸媽都會來尋求我的意見。我能感受到那種無力感慢慢地在我們家消失了。大家仍會爭吵,仍有矛盾,但似乎換了一個思路,遇到問題先去想怎么解決。 今年過年期間,我還和我爸爆發了一次非常大的沖突,我爸答應給家人做幾個菜露露手,但最后又犯懶放棄。所以并不是上上課一切問題都能解決,但起碼我們這次沒有像以前一樣讓矛盾越積越大。幾天后,我向父親道了歉電腦怎么直接重裝系統,他也耐心聽進了我的規勸。 過去,他們只能理解到我工作辛苦,但現在他們更多知道我在做什么,為什么選擇做某件事。當父母從底層上認可你這個人的時候,你獲得的愛與支持,遠遠大于通過關系這層獲得的。 預計到今年五月底,我才能把這本書講完。這個進程比想象中慢很多,畢竟一切是從最基礎開始的。很多朋友知道我給父母上課,會問我哪有那么多時間?怎么堅持下來?我覺得本質是我的價值觀變了,我把它當做一個非常重要且值得長期投入的事情了。我會讓我的時間、精力、資源都往這邊傾斜。以前工作之余桌面壁紙高清全屏電腦,我可能約朋友吃個飯,看個電影,打個游戲,但現在我一想沒什么事干,那不如和父母打個電話、上個課吧。它已經變成我閑暇時間的首要選擇。 我減少了很多社交,接活兒也不太頻繁。我對自己的人生有了更清晰的判斷,只要做好我現在想做的事情就好。我把給鄉村孩子上公益攝影課、給父母家人上家庭教育課,作為人生下半場的重點。還有一個好消息值得分享,我帶的第一屆學生里,有個女孩去年通過攝影特長考上了大學。
報紙版面截圖。 |
|
掃一掃在手機打開當前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