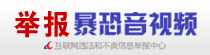從我幼兒園中班起,父母親便開始試探著“往外走”,幾周、幾個月,從杭州、蕪湖,轉到重慶

從我幼兒園中班起,父母親便開始試探著“往外走”,幾周、幾個月,從杭州、蕪湖,轉到重慶。父親想把一家人盡量攏在一起,于是我小學時代輾轉多地。我心里明白他們是為了我以后的發展鋪路,但我的成長一團糟,幾乎成了父親的翻版。上大學前,我從沒談過戀愛,冷漠卻渴望表達,放縱卻努力克制,認識的人都說我特別矛盾。
2001年9月11日凌晨1點,我出生在四川省瀘州市的一個公立醫院。白天,父親躺在家里看到了襲擊美國雙子塔和五角大樓的新聞,“那里面都是全世界的精英啊,說不定我們孩子就是投胎過來的”,他逢人就喋喋不休,自豪于我出身不凡。
母親那時還在醫院里昏迷不醒,產后大出血她要動第二次手術,醫護卻到處找不到我爸的人。情況危急,外婆簽了手術同意書。母親后來向我描述當時的情形:“就是在爬山,我緊緊地拉住繩子。每次快要爬上懸崖的時候,就滑倒,我想起你還那么小,不能沒有我的照顧。最后,拼命咬著牙就上來了,剛好醫生在拍我的臉,說醒醒。”
待我們回到家中,父親仍舊游魂一樣,他連抱我的姿勢都不對,差點把我憋死;好幾次帶我出去轉悠,不是磕壞額頭就是撞壞鼻梁。父親單位分的福利房破舊潮濕,經年累月地漏水,母親坐完月子后,外婆再也忍不了了。臨走前,她對母親說:“孩子他爸不靠譜,也不上心,別指望著他帶孩子。”
父親是90年代西南交大的大學生,機電專業,從峨眉山分校畢業后回瀘州進了一家國營機械廠。我倆溜達時,他總一遍又一遍地描述自己當年多刻苦,中高考他都一枝獨秀,但在愛情上一竅不通。懂事后,我問他大學怎么度過的,父親支支吾吾,“大學女生太少了,沒談戀愛”,出社會相親時才認識我媽。
我媽對他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介紹人說“只大5歲”,但見面后父親佝僂著背,衣著老式、面相老成,像大了10歲不止。同行的朋友說不合適,看著太老了。外公外婆卻很滿意:“這是大學生哦,了不得。”母親從小很聽兩老的話,結婚了。
我打架很猛,長到4歲,只要我受到一點欺負,哪怕對方有幾個人,體格比我大,也要拼到頭破血流,非打回來不可。小孩之間的矛盾雞零狗碎,干了什么壞事也會很快忘記。我心安理得、隨心所欲地搞破壞,為此爸媽給我轉了七八所幼兒園。
周圍人多番數落父親,但小時候我最喜歡的大人就是他——父親會從小攤上給我買好玩的DVD,用臺式機放給我看;教我組裝臺式電腦,給我做計算機啟蒙;追著我喂飯,直跑到公共廣場。幼兒園的多次轉學,就是出自于他“多換個環境,讓小孩有更多接觸的機會”的教育理念。
母親似乎對感情“免疫”,不算冷血,只能說她對愛和子女完全沒有概念,只是匆匆完成著社會給女人的既定任務。父親則進階為“逃避”,現在刷到短視頻里有關感恩或愛的內容,會慌慌張張地劃走。這樣兩個人,很少能站在對方立場上考慮。
母親頭上有個哥哥,而父親是奶奶5個孩子里的老幺,家里把唯一的讀書機會給了他。長大后,我似乎理解了父母那些“固化認知”的因由。叛逆期后,我開始頻繁對抗,并加快逃離。
2008年,父親單位改制,領導班子更替,效益下降,他拿到手的薪水降了一大截。母親中專畢業,一開始在報社上班,后應聘上了沃爾瑪的導購員,再升上領班。我們家的生活勉強過得去,但父母皆不想白白耗著。瀘州就業機會實在有限,他倆決定一起去外地碰碰機遇。
伊始,父母怕萬一他們在外安頓不下來,讓我受苦,我時不時被他們寄放在外公家里。等他們干出點名堂,便回鄉接我。我們搬到新家,漏水潮濕的舊福利房租了出去,新房子寬敞了些,方便叫奶奶來照顧我了。
等到我上小學時,他倆又摸索到了一個去杭州的路子,我則開始了長期在外公家的寄住生活。父母拎著包,我哭著拽衣角不讓他們走,他倆安慰了我幾句,便不再回頭。外公用力把我拽開,我從窗戶往下喊:“要早點回來啊。”直到他們消失在小區大門外的盡頭。
幼兒園時轉學過多,我沒留下一個好朋友。小學開學報到,外婆領著我,看著其他小朋友呼朋引伴,我第一次嘗到了膽怯的滋味。外公家三代同堂,外公外婆、舅舅舅媽、表妹分別占據一間臥室,所以我只能一直睡沙發。環境氛圍突變,又得學著瞧別人眼色行事,我吃不下飯、睡不了覺,隔壁姨婆來哄,才騙我吃下第一口。
我家里的寶貝臺式電腦被搬到外公家客廳,但再沒人領我去買DVD了。有次舅媽心血來潮,我又按又擰,機子反應極慢,界面亮起來后顏色暗淡,明顯發潮荒廢了。舅媽打開了單機紙牌游戲,鼠標點了幾下便“呲”地黑屏了,再無法亮起。我確信,我的好朋友——電腦里那些蹦蹦跳跳的小人,就此永別了。
外公和舅舅進了縣城,在長江起重機廠打工,但骨子里仍是鄉村那套節衣縮食、棍棒教育的理念,一點兒雞毛蒜皮做得不合他們心意,便“賞”我一頓打,一天一小打,三天一大打。落差如此之大,我每天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漸漸地,我學會了偽裝,跟從于他們的“美德”,掉了一顆飯,就趕緊撿起來吃掉。
大多數時候,動手打我的都是外公,“棍棒底下出孝子”,舅舅和媽媽都是這樣過來的。舅舅性格也暴躁,看不慣時也拎著竹鞭對我一頓抽。他們甚至拔掉了電話線,因為只有我父母會打來,我接了就不讓掛。那時我不理解,后來才知僅僅是因為長途電話費很貴。他們的暴戾恣睢,讓我覺得很壓抑、害怕。我向父母求助,他倆說,“習慣了就好,你會獨立的”;我說被打了,他倆說,“好了好了,我們先掛了,你記得吃飯”。
我渴求甜味,卻被他倆灌了一包水泥,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失望。長大后,我把“獨立”踐行到極致,什么都靠自己,也堅信自己能夠做好。
表妹小我兩歲,也皮,我們常和小區同伴一起玩捉迷藏,在新搬回家的電腦上玩“4399”。出門時,她也惦念著我,怕我太孤獨;生病了,她喝一口枇杷止咳糖漿,也給我塞一小杯,因為很甜。
臨到節假日,舅舅舅媽帶著她,外公外婆則帶著我,兩撥人分開過。外公外婆在農村有眾多親戚,也可能是看我太苦相,每次“走人府(走親戚)”時都一定會把我帶上,試圖以此來提振我的“士氣”。這個舅舅、那個姑媽,只要有一家辦宴席,外公外婆就去“隨份子”,我就順便蹭吃蹭喝,在陌生環境里住好幾天。
有次,他們帶我走了一個很遠的親戚。親戚家一兒一女,玩耍時意外把我的左眼劃傷了,疼得我睜不開眼。大人們也沒說帶著我看醫生,先用土法子搗鼓,直到徒勞無益,女主人才慌了,怕我父母追責,先是安撫我,要我自認調皮,與他們無關,然后給外婆倒貼紅包,撿了些土雞蛋和蔬菜,讓她幫著圓謊。
回去的路上,外公外婆打雞罵狗,外公還逮住我,要強行把我左眼掰開,外婆則在一旁祈禱“阿彌陀佛,菩薩保佑”,我的左眼更疼了。到家后,左眼照舊睜不開,外婆破天荒地讓我給父母打了電話,受傷的理由換了一個——是我自己擱幼兒園撞墻上了。
幸好,調養幾天后,我的眼睛能睜開了,所有大人都長舒一口氣。外婆說這都要歸功于她平日里去廟里拜神、拜菩薩,拜得勤快,上天顯靈。
父母只有過年時才會回來,他倆帶著給我和表妹的新衣服,零嘴小吃,不斷描繪著異鄉見聞。外公外婆、舅舅舅媽反應不咸不淡、零零落落,話題不得已轉向養老保險、子女教育。外公當著他們面,難得夸我:“這孩子很懂節約,每天給他3塊錢的路費,總等最便宜的公交,來回只要2塊錢。他這學期攢了50塊,讓我幫著存著交給你們。”
團圓飯吃完,父親收了我辛苦攢下的50塊錢,偷偷把我拽到一個角落,說:“(你)外婆他們很勢利,每月給他們打了1000塊做你的生活費,可你現在還是這么瘦。他們喜歡在外面‘打腫臉充胖子’,給XX結婚時送了3次(紅包),他們500塊,舅舅家500,你媽1000。”
“因為(你)外婆總覺得你媽在外面掙了大錢,其實我們在杭州也存不下多少。杭州不適合我們,很快就要換城市了。(我覺得)你在這里過得不好,等我們立穩了腳跟,到時候再把你轉學過去。”父親也不管我能不能聽懂的算計,自顧自地敘述著。
一股陌生的氣息從父親身上散發出來,自他毫不猶豫收下我的錢開始,他似乎不再像以前那么溫柔,面目可親。
母親日常泡在父親的抱怨里,轉頭就向外婆交了底。他們一走,外婆就沖我嘀咕:“說些什么,說我沒有照顧好你的生活,克扣你的生活費。哎呀!早知道你這次春節就跟他們一起去杭州唄!”外公也附和:“說再多也沒有用!外孫外孫,為什么要加個外字?畢竟沒有親的那么好啊。”
這種不受待見的生活,讓我愈發寢食難安,我做夢都想逃離外公家。可兩年后,我才等來心心念念的轉學。
班主任劉老師教語文,每天放學前都要把一眾孩子趕去操場,排列整齊后才慢悠悠地向我們強調作業、規矩,再說些有的沒的,才讓一旁久等的家長領人。我個頭矮站在第一排,聞著他的口臭,承接橫飛的唾沫。劉老師精熟表面功夫,像某個央視兒童節目的主持人,轉臉就對學生圖窮匕見。
在外公家寄住久了,他們越發對我膩煩,表妹大了,我支愣在客廳也不是個事兒,挨教訓的次數水漲船高。父母也覺得我太“造孽(可憐)”,瀘州實驗小學在我出生那所醫院下面,離外公家很遠,我每天早上6點起,坐40分鐘公交,跌跌晃晃地趕到學校,傍晚再趕回去。
父母費了一番工夫打聽,托管班只負責學生午休和放學后的2個小時,直到聽人說,劉老師家寄宿了一個學生,他們就忙不迭想把我也送去。劉老師淡淡應下了,雖嫌錢少,他體諒我父母打工不容易,就忍了。外公那邊已對我全無好感,自然沒有太多挽留。
父母覺得為我尋了一個好去處,我卻覺得這陌生冰冷的環境跟外公家差不多。我才8歲,卻早已習慣了寄人籬下的生活。我對劉老師更加順從,他給我和寄宿同學布置了額外的作業——寫大字,背莫名其妙的詩歌,閱讀名著寫800字讀后感,輕輕松松占去我的休息時間。當時少兒頻道正播著《豬豬俠》《果寶特攻》,沒有我的份,電腦更是摸不著。
不過至少,書籍中的瑰麗故事拯救了我,“白雪公主”“小豆豆”“小王子”的境遇讓我覺得自己也能等到未來,但這一切截止在晚上9點半——劉老師會關燈關門。
我時常饑餓,一種精神和身體上雙重的餓。有次劉老師夫婦外出,我和那個同學待在家,我順手拿起一根面包吃掉,就像同學做的那樣。劉老師夫妻倆回來后,指著茶幾上放面包的位置,眼神凌厲,叱罵我:“沒有跟我們說,就拿桌上的面包吃了嗎?這種行為叫偷!”
我問同學為什么能吃,師母瞥我一眼,說:“別人一月生活費交3000,你交1500,這能比嗎?還有你別忘了,生病、資料、衣物的錢還得自己出。你父母給的不夠,上次生病都是我們掏的錢。”
打工間隙,父親回老家辦事順便看我,他提著牛奶水果,劉老師便戴上面具,收禮、討好、試探。父親一走,他又恢復尖酸刻薄,父親送的牛奶水果,我還是沒有份。
我老是不由得把自己代入童話里悲慘主角的境地,幻想著能改變故事的走向。可惜,幻想終究被沉悶現實打敗。
二年級結束了,父親剛好來接我放學,一見面,我就飛快地撲了上去,但他只是木訥地站著,一點兒高興的樣子都不愿意裝出來。那幾天,我生病發燒,拉他陪我打針,他一路責怪我為什么生病了。我低著頭不說話,直到針扎進,眼淚才不受控地涌了出來。
打針的姐姐為我圓場:“之前兩天都是一個人來的,怎么今天打針就哭了,是因為見到爸爸太激動了嗎?”
三年級時,我轉學到蕪湖,終于和父母團聚了。蕪湖是安徽的第二大城市,從一年級開始就學英語。轉去的公辦學校不打算收我,可我爸工作單位跟他們有合作關系,最后還是把我“通融”進去了。
頭天晚上,我對新的學校尚存著些期待,結果第二天在教室里只收了些嫌棄和冷眼,甚至連課桌和椅子都沒有。班里的男同學們圍著我,一個男同學走上前假意問我從哪兒來的,我的回答還沒出口,他一腳就把我踹倒了,我倒在地上,骨頭疼,勉力爬起來拍了拍新衣服上的腳印、灰塵。直到下一節英語課老師進來,他們才一哄而散。
我腦子里嗡嗡的,根本聽不清老師說的什么,下課后也不敢找人問,隔天被留堂,我又悄悄溜走了。英語老師的排外毫不掩飾,在他們眼里,我只是一個鄉下來的土包子、差生。我惶惶不安,但心里明鏡一樣,跟父母告狀也沒用——他們接到英語老師電話后,狠狠地罵了我一頓。
第四天中午,英語老師找來,把我扯到教室外面,拿一把大人手掌寬的教學直尺打我手心,打一遍問我一遍,直到我雙臂都漲得疼痛。
我從零學起,音標自己買錄音帶。學習上指望不上父母,他們一個大學生、一個中專生,卻只是迫不及待地把我丟去托管機構,回家再惡狠狠地提問。父親變化很大,我才發現他如此暴戾,動輒在公共場合大吼大鬧。我一度覺得很羞恥,但我也莫名學會了。叛逆時,也習慣了惡語相向,根本不顧引起了路人多大的反應。
在蕪湖求學的時光,父母的關系也不太平。母親吃不慣蕪湖的飲食,一心想回到重慶,發展機遇更大,離瀘州也近,父親想要再緩一緩。
一次他們吵得激烈時,不知道是誰用力把裝著剛炒好菜的不銹鋼碗“哐當”扔在地上。我們一家和父親的一個同事合租,那個同事會自覺把房門緊閉。這樣的次數多了,我能迅速抓到苗頭,提前把菜端進廚房,以此減少硝煙過后我打掃衛生的難度。父母還存著一絲羞恥心,轉移到臥室邊吵邊砸,手邊硬的軟的,花瓶、遙控器、枕頭……統統往對方身上擲去。有次我站在中間勸架,被遙控器砸到頭,頓時哭了起來,然后我媽抱著我喊:“幺兒,疼不疼?”
從此之后,我竟生出了些奇怪想法——我樂意他們吵架,更巴不得他們又把東西砸在我身上,這能讓我獲得一絲久違的溫暖。
母親那時在“郎酒”上班,職位是營銷經理,需要參加很多酒局,一回到出租屋就鉆進衛生間吐得昏天黑地。2010年前后,酒水行業十分賺錢,吃喝盛行,像我媽那樣能喝,工資自然水漲船高,家里經濟地位變化,父親嫉妒母親,便耍起了脾氣。母親這樣辛苦,他還看不起,總對著我貶低她是“三陪”,天天在外“鬼混”,然后安然躺在沙發上看電視。合租同事都看不下去,用開玩笑的語氣勸:“老楊,學下你的兒子。”我在一旁趕緊扶著母親進臥室,倒水、拿盆子,讓她能舒服一些。
在那種情境下,我開始刻意回避有關情感的一切,性格越發膽怯,被欺辱也不敢反抗。當我們一家人勉強坐在一起看電視,遇上溫情的廣告,我會比父親更快調走。生活飲食的差異和孤獨,竟讓我在一瞬間想念起了瀘州。雖然瀘州沒啥美好回憶,但那一點點熟悉感也比漂泊強太多。
我的境遇很快否極泰來電腦主機結構示意圖。母親跟我說:“這邊應酬工作太重,我決定還是回離瀘州更近的城市發展。”她砍瓜切菜般調回重慶,又聯系上了劉老師,準備花錢把我重新插回瀘州實驗小學。
父親無力阻止,只能趁我媽不在時,多次策動我:“我看你在老家待著并不好,把你帶在身邊改善伙食,但你媽總說蕪湖不適合她。你可別被你媽帶跑了!”
但這事一路暢通——雖然我在蕪湖的學習剛剛有了起色,跑步得了全班第一,學校想發展我做體育特長生,因為期末考試考了90分,英語老師也一改往日態度,甚至有女同學向我表白——可三年級的孩子哪能生出幾分主見?我心里對父親叨叨的有點認可,因為這里的教學水平好太多。
可惜沒有如果。回瀘州自然要去外公家,迎接我們的是舅舅的嘲笑。飯桌上,他們問母親:“外面有什么好,現在還不是又把孩子送回來了?”
小城市的人確實是這樣,年輕時候不出去闖,過幾年后愈發膽怯。就像我的堂哥,大學一畢業,就只想回瀘州當小學體育老師。
這次,父母把我送去了奶奶家,不用再睡沙發了。我媽想等著父親也調回重慶再一家團聚,那又是一年。
奶奶家是典型的農村自建房,三樓有2個房間,我暫住堂哥那間。奶奶住二樓。門口是公交站牌,四周有田野、池塘。每天有很多跟我一般大的孩子,和我一起坐40分鐘的車到學校。平時家里沒有其他大人,我就幫著奶奶割草喂豬,打理農活。
母親回老家附近出差,有時能待上一周多,便接我去找其他親戚家的小孩玩。大人們坐一起聊天,我偶然窺到有個叔叔偷偷親母親的臉,于是故意在他們面前晃,咳嗽了一聲,那個叔叔的動作戛然而止。我后來偷偷把這事告訴父親,他卻很無力:“真的嗎?你當時還看到別的沒有?我現在還不能跟那個人鬧翻臉。”
奶奶待我不錯,但面對著曠野,我常感到孤獨。奶奶70多歲了,身上總有這樣那樣的小毛病,去醫院也查不出所以然。父親口頭很關心奶奶,說些“保重身體”的場面話,但幾乎從不主動帶她去醫院。我一提起,他就反問:“你是孫子,你怎么不帶去?”外婆評價他:“不是‘晃晃兒(混混)’,但太死板了,辦事不靠譜。”
四年級下學期,我打籃球時,一個小孩不知道被誰推搡,沖過來撞到我后背上,又彈落在地,胳膊磕在水泥地上。我扶著他去校醫室,校醫治不了,送去大醫院被判定為骨折。那小孩什么都不懂,只記下了我的名字以及我當時說的“對不起”。班主任帶我去醫院看他,他媽也在,沒為難我,但要學校有個交代。學校翻了幾番,小孩當時正跟著一群同學瘋跑,他害怕不說,所以也沒找到真正的肇事者。他父母便調轉矛頭對準了我。
父親一輩子搞不好交際,他知道以后竟然把手機關了,想藉此息事寧人,反倒讓那小孩父母覺得我們做賊心虛。待父親被對方找到后,兩家人上談判桌,一開始協商,賠幾千。父親這才反復詢問我當時的情形,還找來一起打球的同學。確認了錯不在我之后,他就又不接對方電話了——他想著,我下學期要轉學去重慶,拖著拖著,就煙消云散了。
之后我插到了重慶的一所新成立的小學,那個學校招不滿生,所以很樂意接收我們這些轉學的學生。本來要面試,但招生老師聽到我800米跑了第六名時眼睛一亮,他質疑成績單上體育才60分,我急中生智解釋道:“那是同學幫著打的分,隨便打的。”
新小學的轉學生很多,20多個,都是因為父母來重慶務工跟著來的,這就讓我少去了在蕪湖時被本地孩子小團體騷擾霸凌之憂——但在我們班體育老師面前依舊不能幸免。跟在父母身邊后,我長高了不少,臉上有了紅潤,學校也想推我去當體育特長生,專攻400米。我又做了班里足球隊的隊長,比賽時擊敗了體育老師帶的那個班。那次踢完后,他惱羞成怒,專門喝了口水噴在我頭上,還不顧形象破口大罵。
新小學的生活快樂不少,我交了一些朋友,帶領足球隊踢贏了其他兩個班,校運會拿了400米和800米的第一名。往昔的陰翳,一掃而空。
但父母吵架更厲害了,父親追著我媽“查崗”,一個電話沒接,他就奪命連環call,然后轉過頭帶著哭腔跟我說:“你媽不要你了,不知道她在外面干什么。”母親一到家,他必然像一樣盤問她的行蹤。老戲碼在重慶家里上演,打架,砸飯菜,他們開始把“離婚”掛在嘴邊電腦主機結構示意圖。
打籃球的舊賬重提,因為父親辦事不得力,我走后,瀘州實驗小學順水推舟徹底把問題拋給我們兩家,并扯謊說我們畏罪潛逃。這讓對方死死咬住了我們,非得爭個好歹。多輪協商無果后,他們把我們一家告上了法庭,我們得不斷回瀘州應訴取證。
我媽氣不打一處來,罵道:“說了多少次了,這件事情私了最好。當時大不了就3千,現在搞成要我們賠4萬了!”
“要是當時就妥協了,后面還有源源不斷的麻煩要我們賠錢怎么辦呢?”父親也不服氣,“我相信中國的司法系統,會還我們一個公正!”
開庭后電腦主機結構示意圖,由于雙方當事人均為未成年人,我和那小孩都沒出庭。庭審結束,我問外婆:“我們贏了嗎?”外婆喃喃:“贏了,贏了。”父母卻陰著一張臉不說話。
最后我才知道,父親沒等來他的“正義”,法院選擇兩邊各打一大板,對方借著在部隊的關系,判我們賠2萬。家里所有的親戚大人輪番指責我,問我為什么要道歉?為什么要扶起那個該死的小孩?
這些恥辱感不斷撕扯著我,我下決心以后得更加冷漠才行。父母也變了,這件事情結束之后,他們對我更少有溫情,父親甚至習慣了在公共場合對我大吼大叫。
但過年少不得還得回瀘州。可能因為當體育生的緣故,我個頭躥得很快,身材高大了不少。外公對我的態度發生了180°大轉彎,抱著我高興地喊,“外孫長大了呀!長得比我還高了!”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恩寵,我手足無措。還有就是,我與表妹竟無話可說了,邁入青春期了,我們各自有了不同的圈子。
之后每次回瀘州,童年的黑暗記憶就會沉渣泛起。我蠻不理解,大人們在我幼年時做的那些事情,怎么可能就這樣輕易地蒸發掉了呢?大人都說,是因為你做了錯事,才會打你。
這些作踐,讓我比同齡人更早熟些。我愛上了歷史書,樂此不疲揣摩那些政客英雄,我長精,知道該說什么不該說什么。在新環境脫穎而出后,我開始做一些嘩眾取寵的行為博關注,為逗笑身邊同學,公然捉弄挑逗女生。
小升初時,父親給市一中上報我是體育特長生,回來沾沾自喜走上了后門,讓我好好把握。我十分反感,我本來就是正當競爭,沒必要把我碾進泥里。但我沒算到,考試時我發燒了,800米被對手反超一大截。我哭著跑完全程,跌跌撞撞走向父母,他倆竟然在那一刻,雙雙側著身子躲開了。
“你是個屁的體尖生,連小姑娘都跑不過。”父親見實在躲不過,從上往下鄙夷地瞅著我,“白給你機會了,浪費我的車費。”
上初中后,我再也不提自己曾是體育尖子生了,也放棄了這條路。我開始寄宿,剛開始室友們躲在被子里偷偷哭,我卻因變成一個人、遠離過去而興奮。這次,耳邊再也沒有喋喋不休的說教了。
除了踢足球,周末和寒暑假我就窩在家里上網、看小說、打游戲。我在游戲里認識了幾個年齡相近的網友,聊天才發現他們的生活好輕松,根本沒有我這么多要累的事情。
我也喜歡上了看網文,瀏覽各大網站里的科幻、懸疑、古風、言情小說,有次在熱榜上看到一篇網文朝代錯亂,就主動聯系了那個寫手,他把我拉進他的“十人忠實粉絲群”,幫忙試讀。
我也萌發了自己寫作的,散文、讀后感、小說,我都搗騰了些,之后就是寫連載小說,我會花上大半個晚自習的時間寫,第一波讀者就是我的同學們。父親開家長會后意外知道了我寫小說,又是劈頭蓋腦一頓訓斥。
更糟糕的是,我近視加深了,之前跟父母提配眼鏡,他們覺得浪費錢,我強撐著若無其事地生活學習。無奈再提了一次,父母暴怒之后帶我去了眼鏡店,一查200度。在店里,父親吼:“敗家子,現在又是近視眼了。”
中考是先填志愿后出分,父母為了求穩,只填了西南大學附屬中學——因為之前簽了學校降10分的協議。實際出分,我的成績比預期更高,但木已成舟。
暑假時,我參加學校的夏令營并通過了開學測試,考到了“清北班”。父親又搬出那套“別人看你是外校來的,給你一個‘清北班’的機會,看你抓不抓得住咯”,我異常難受、自卑,像是我高攀了一樣。
西大附中屬于重慶高中“七龍珠”之一,同學們表面和睦交好,實則暗流涌動。4個“清北班”206個學生,大部分都是初中部直升。我再一次成了外來者,每天要花大把的時間暗中角力。
成績掉到了前400,父母老生常談,認為我不夠聽話,得知我重操寫作舊業,斥罵:“不務正業!”如此這般,我都不愿同他們耍心眼。我準備參加《萌芽》的新概念作文大賽,央求他們幫我郵寄文稿,但等待我的是:
童年的顛沛流離,讓我總期待著換個新環境,這樣仿佛能帶給我新生一樣。父母要我高考前別談戀愛,上大學后認識了女友,父母又嫌棄她是福建人。如今回想,生活有太多不如意,父母也有自己的苦衷,相比于死守的舅舅舅媽,他們勇敢太多,給了我新環境。但我仍舊只想逃離,還想逃得更遠一些。
關于“人間”(the Livings)非虛構寫作平臺的寫作計劃、題目設想、合作意向、費用協商等等,請致信:/p>
投稿文章需保證內容及全部內容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人物關系、事件經過、細節發展等所有元素)的真實性,保證作品不存在任何虛構內容。
財聯社2月14日電平板電腦二合一,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法國致力于向印度提供最好的技術,法國公司將在能源轉型和碳中和方面積極幫助印度。
財聯社2月14日電,據路透調查顯示,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以43%的支持率在共和黨2024年總統候選人提名中暫時領先;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支持率為31...
免責聲明:本站所有信息均搜集自互聯網,并不代表本站觀點,本站不對其真實合法性負責。如有信息侵犯了您的權益,請告知,本站將立刻處理。聯系QQ:1640731186